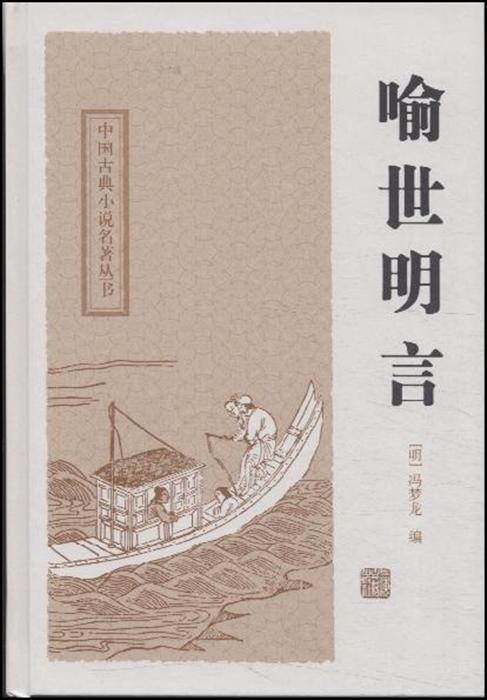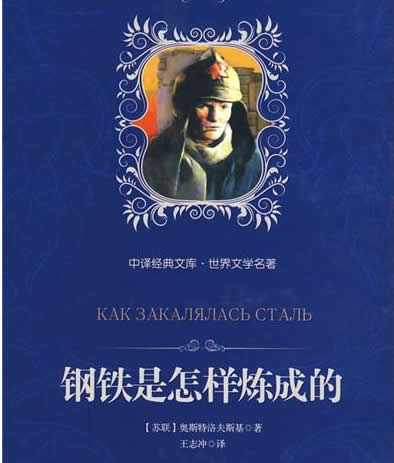- 第十七章 从合恩角到亚马逊河口
-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到平台上来的。可能是加拿大人把我背上来的。我呼吸着,我吸着海上的新鲜空气。我的两个同伴在我身边,他们也沉醉在这清新的空气中。那些长时间缺乏食物的不幸的人们,别人第一次给他们提供食物时,他们不能无节制地吃。而我们却相反,我们没必要节制,我们可以大口大口地呼吸大气中的氧气。是微风,正是微风给我们送来了这份神迷的陶醉!
“啊!”康塞尔说,“多好啊,氧气!先生不用担心呼吸了!人人都可以呼吸了!”
尼德·兰呢,他没有说话。但他的嘴张得很大,鲨鱼看了都会害怕。他那是多么充分的呼吸啊!加拿大人就像一座熊熊燃烧的火炉一样,消耗着氧气。
我们很快就恢复了元气,我看了看周围,发现就我们三个人在平台上。没有一个船组人员,尼摩船长也不在:没有人出来享受这外面空旷的空气。这些奇怪的“鹦鹉螺号”水手,他们只要船内流通着空气,就满足了。
此时我一开口便向我的两个同伴表达我的谢意和感激。尼德和康塞尔曾在我弥留之际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延长了我的生命,现在即使我说出所有感激的话言,也报答不了如此的一种奉献。
“好啦!教授先生,”尼德·兰回答说,“这不值一提!对此我们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呢?没有。这只是一个算术的问题。您的生命比我们的生命更有价值。那么就应该把空气留给您。”
“不,尼德,”我回答,“我的生命并非那么有价值。没有什么比一个慷慨善良的人更有价值,您就是这类人。”
“好啦!好啦!”加拿大人局促不安地重复着说。
“而你,我忠实的康塞尔,您也受了不少苦。”
“跟先生您说白了,我没受多少苦。我只是少呼吸了几口空气,但我相信我能顶过去。再说,我一看到先生晕过去,就一点儿想呼吸的欲望也没了。这就像人们说的,我断了呼吸……”
康塞尔觉得自己说得太平庸了,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停嘴不说了。
“我的朋友们,”我非常激动地说,“我们永远心连心,而且你们有权发落我……”
“我会使用这个权力的。”加拿大人马上说。
“什么?”康塞尔说。
“是的,”尼德·兰接着说,“当我要离开这地狱般的‘鹦鹉螺号’时,我有权拉着您跟我一起走。”
“好了,”康塞尔说,“可我们的方向走对吗?”
“是走对的,”我回答说,“我们正朝着有太阳的方向行驶,我说的太阳,是指北边。”
“可能吧,”尼德·兰回答说,“不过还必须知道我们是否返回太平洋还是大西洋,也就是说有人烟的海域还是没有人烟的海域。”
对于这问题,我无法回答,我担心尼摩船长更宁愿把我们带到濒临亚洲和美洲海岸的那片辽阔海洋中。这样他就可以完成他的海底环旅,然后回到一处“鹦鹉螺号”觉得最自由自在的海域中。但如果我们回到太平洋,远离人类居住的陆地,那尼德·兰的计划将怎么实施呢?
不过不久,我们就会明确这重要的一点。“鹦鹉螺号”船只正快速前进。一会儿,它就穿过了南极圈,把船头朝着合恩角开去。3月31日晚上7点,我们到了那个美洲的岬角。
到了此时,我们的过去所有的痛苦都被忘记了,被困在冰层里的记忆已经被我们从心里抹掉了,我们现在关心的只是未来。尼摩船长不再在客厅里露面,也不再出现在平台上。每天都由大副出来测定船的方位并把它记在平面地图上,我由此知道了“鹦鹉螺号”的确切位置。而且那天晚上,我们又沿着大西洋的原路返回走,这使我非常满意。
我把我观察到的结果告诉了加拿大人和康塞尔。
“好消息,”加拿大人回答说,“但‘鹦鹉螺号’要去哪里呢?”
“我说不来,尼德。”
“去了南极后,船长难道想去北极,再从著名的西北通道去太平洋?”
“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康塞尔说。
“那好!”加拿大人说,“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奉陪他了。”
“总之,”康塞尔补充说,“尼摩船长是个杰出的人物,认识他我们并不后悔。”
“特别是在我们离开他之后。”尼德·兰揶揄道。
第二天,4月1日,“鹦鹉螺号”船只在正午前几分钟浮出了水面。我们在西面看到了海岸。那是火地岛,早期的航海家看到岛上上著的茅屋上飘起无数的浓烟,便给它起了这个名字。火地岛是一个30里长、80里宽的大岛群,处在南纬53度到56度、西经67.5到77.15度之间。我觉得这个岛的海岸很低,但在远处矗立着一些高山。我甚至相信我看到了海拔高度为2070米的萨尔眠图山,那像是一个片岩金字塔,峰顶很尖。尼德·兰跟我说,人们根据山上是云雾缭绕还是没有云雾,就能预报出是坏天气还是好天气。
“真是一个好晴雨表,我的朋友。”
“是的,先生,这是一个天然的晴雨表,当我行船通过麦哲伦海峡时,它就从来没有预报错过天气。”
这时,这座尖峰似乎清晰地从天底上显露出来。这是好天气的预兆。会有好天气的。
不久,“鹦鹉螺号”船只重新回到了水中。它向海岸靠近,但只是沿着海岸走了几海里。这时,通过客厅的玻璃,我看到了一些长长的海藤和一些巨大的墨角藻——梨形藻的一种,南极的自由海中就有几种梨形藻种类,它们算上粘性光滑的根须,长度竟可达到300米,它们可是一种真正的铁缆,比拇指还粗,非常坚韧,经常用来做船缆。另外还有一种名叫维尔普的海草,它的叶子长4英尺,粘在珊瑚的分泌物里,铺在海底上;这种草是上千万种甲壳动物、软体动物、螃蟹和乌贼的窝巢和食物。在那边,海豹们和水獭们正按照英国人的饮食方式,把鱼肉夹上海草,美美地大吃特吃呢。
在这片动植物繁多的海底,“鹦鹉螺号”船只以特别快的速度行驶着。傍晚,它就接近了马鲁因群岛。第二天,我便可以观察到岛上的峻峰。马鲁因群岛可能是著名的约翰,大卫发现的,他把这个群岛命名为大卫南群岛。后来,理查德·霍金把它叫做梅当岛,即贞女的意思。后来,18世纪初,圣一马洛的渔夫又称它为马鲁因岛。最后,它被英国人占有了,现在英国人又叫它为福克兰群岛。这里海并不太深,我于是想——这不是没理由的——,这两千周围遍布着大量小岛的岛屿,以前曾是麦哲伦陆地的一部分。
在海岸边上,我们船上的鱼网拖上来了一些美丽的海藻种类,特别是一种根部拖着世界上最好味的贻贝的墨角藻。同时,有十几只海鹅和海鸭被我们打了下来,它们在平台上挣扎着,一会儿就被送进了船上的厨房。至于鱼类,我除了特别注意到一种属于虾虎鱼类的骨鱼外,还尤其注意到一些长两分米的球鱼,它们全身布满着黄色和白灰色的斑点。
我还欣赏了无数的水母。马鲁因海中特有的茧形水母是世上最漂亮的水母。它们有时看是一把非常光滑的半球形太阳伞,滚着几道红褐色的花边,缀着十二朵规则的小花;有时却是一个翻转的花蓝,花蓝中优美地伸出一些大红叶子和红色的长细枝条。它们摆动着四条叶状触足游动着,丰富的触须四处飘散着。我本来想保存这类美丽的植虫动物的几个种类;但它们是游云,是掠影,是影子,离开了生它们养它们的大海就会融化、消失的。
当马鲁因群岛的最后几座高峰在海平面消失时,“鹦鹉螺号”船只又潜入了20至25米深的海中,沿着美洲海岸行驶。此时尼摩船长还是没露面。
4月3日之前,我们的船一直没离开过巴塔哥尼海域,它时而潜在海中,时而浮出水面。不久,“鹦鹉螺号”就驶过了普拉塔河河口的大喇叭形海口。4月4日,它来到了乌拉圭附近,但距离海岸还有50海里。它沿着南美洲曲折漫长的海岸线始终向北行驶。这样,我们从日本海出发至今,已经走了16000里路了。
早上约11点,我们沿西经37度穿过了南回归线,走过了佛里奥岬的海面。令尼德·兰最为不满的是,尼摩船长不喜欢让船靠近有人居住的巴西海岸,他让船速度吓人地向前开去。这样,不论是鱼、小鸟,还是速度最快的别的动物,都跟不上我们的船,这一片海里的自然奇观全部逃过了我们的视界。
这样飞快的速度一直保持了好几天。4月9日晚上,我们已经望到了南美洲最东点的圣罗克角海岬。但这时“鹦鹉螺号”又重新躲起来,它潜入了更深的海底,去寻找位于圣罗克角和非洲海岸边塞拉利昂之间的一座海底山谷。这座山谷在安第列斯群岛的同一纬度上分叉,一直延伸到北面一片9000米长的大洼地。在这个地方,海底的地质断层形成了一处长6公里、一直延伸到小安第列斯群岛的非常陡峭的断崖;而且,在青角岛的同一水平线上,还有另一座不可忽视的断壁,这两个断崖就这样把沉没的大西洋城围了起来。这片海底大山谷里点缀着几座风景如画的海底山峰。至于这些情况,我主要是根据“鹦鹉螺号”船上图书室收藏的一张手绘地图来讲述的,这张地图显然是根据尼摩船长个人的观察,出自于他的手。
这两天内,我们用纵斜机板潜入这片荒芜、深邃的海区里参观。“鹦鹉螺号”能沿着它的对角线做曲线形运动潜到海底的任何深度。但4月11日,它突然浮出水面,我们发觉陆地在亚马逊河口——河水输出量非常大、把海洋好几里内的咸水都冲淡的大河口——重现了。
我们穿过了赤道。在西面20海里处,是法属圭亚那群岛,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上面找到一处藏身之所。但风一阵阵地吹,汹涌的海涛并不容许一只普通的小艇去冒险。尼德·兰可能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什么也没跟我提。我呢,我也不对他的逃跑计划做任何暗示,因为我不想怂恿他去尝试那必定会流产的计划。
我很容易地通过一些有趣的研究来弥补这次迟误的遗憾。在4月11日和12日这两天里,“鹦鹉螺号”一直浮在水面上,船上的渔网战果赫赫地拖上来了大量的植虫动物、鱼类和爬行类动物。
有些植虫动物是被渔网的绳索拖上来的。里面大部分是一些属于海菟葵科的漂亮须形海藻;而在其他的种类中,有源于这片海域的被带须形海藻,它的圆筒状茎很小,装饰着一些直纹和红斑点,头上冠着一片艳丽的触须花饰。至于软体动物,都是一些我已经观察过的种类,像锥螺;身上有规则交叉条纹、底壳有明显突出的红点的岩蛤;活像被吓呆了的蝎子的任性的蜘蛛螺;半透明的石英螺;船蛸;非常好吃的墨鱼;某类枪乌贼——古代博物学家曾在飞鱼中捕捉过这类枪乌贼,它们主要是用来做捕捉鳕鱼的诱饵。
在我还没有机会研究的这一海域的鱼类里,我记录了几个不同的种类。像软骨鱼类,有:化石花斑鱼,鳗鱼的一种,长15英寸,头灰绿色,鳍紫色,背部灰蓝色,腹部白褐色,布满显目的斑点,眼膜周围有一圈金边,这类奇特的动物肯定是被亚马逊河水带到海中来的,因为它们一般是生活在淡水中的;多瘤鳐鱼,喙尖,尾长而细,有一根齿形利刺;长1米的小角鲨,皮灰白色,排成好几列的牙齿像后部弯曲,俗名是拖鞋鱼;蝙蝠鲼鱼,一种等腰三角形的淡红色鱼,半米长,胸鳍长在突出的肉上,使它看上去有点像蝙蝠,但它们长在鼻孔附近的角质触须,使它又有三角鱼的绰号;最后是几类鳞鲺,两侧闪着鲜艳的金黄色斑点;和鲜明的紫色酸刺鱼,它的色泽柔和,像鸽子喉部的颜色一样。
我现在要用我观察到的一组多骨鱼来结束这些有些枯燥、但十分准确的分类:属无翼鳍属的巴桑鱼,喙很圆而且雪白,皮是美丽的黑缎,长着一条非常细长的肉带;长刺的齿状鱼,一种长3分米的沙丁鱼,身上银光闪闪的;卵形鲭鱼,长着两根肛鳍;浑身黑色的黑牙刺鱼,人们要打着麦杆火把才能钓到的鱼,它长2米,肉肥白结实,新鲜时的味道有点像鳗鱼,晾干后就像熏鲑鱼;半红色的隆头鱼,只有脊鳍和肛鳍下面长着鱼鳞;身上交错闪着红白光泽和金银鱼的光泽的茧鱼;金尾鲷鱼,肉特别鲜嫩,它们身上的磷光在,海水中闪闪发亮;舌头细小,浑身橙黄色的波普鲷鱼;尾鳍金黄色的石龙鱼,黑色的硬鳍鱼,苏里南群岛的突眼鱼,等等。
“等等”这个词并不能阻止我还想举出一种让康塞尔记忆犹新的鱼,这里头是有原因的。
当时,我们的渔网拖上来了一种很扁平的鳐鱼。这种鱼如果割掉尾巴,就是一只完美的圆碟。它重达20几公斤,下部白色,上部浅红色,有深蓝色的大圆点,圆点外圈着黑色的圆圈,皮很光滑,尾部是一支分成两叉的鳍。它被摊在平台上,不断地挣扎,抽搐着想翻过身来,它费了很大的劲,最后一跃,差点蹦到海里去了。但看管着鱼的康塞尔扑了上去,我还没来得及拦住他,他就两手把鱼捉住了。
一下子,他就被打翻在地,四脚朝天,半个身子都麻痹了,嘴里叫道:
“啊!我的主人啊,我的主人啊!快来救我。”
这是这个可怜的小伙子第一次不用“第三人称”来跟我讲话。
我和加拿大人赶紧把他扶起来,用力给他按摩。当他缓过神时,这位永远的分类人便结结巴巴地低声说道:
“软骨纲,软鳍目,固定鳃,横口次目,鳐鱼科,电鳐属。”
“是的,我的朋友,”我回答说,“这是一条把你电成如此地步的电鳐。”
“啊!先生相信我,”康塞尔马上说,“但我一定要报复这只动物。”
“怎样报复?”
“把它吃掉。”
当天晚上他真的这么做了,但这是出于纯粹的报复之心,因为坦率地说,那肉简直是啃不动。
不幸的康塞尔是受到了一种最危险的电鳐的袭击,这条鱼叫伞形电鳐。这种古怪的动物,在诸如水这样的导体中,在几米远就能电击其他的鱼,它发电的器官功能无比的强大,身体主要部位的带电面积绝不小于27平方英尺。
第二天,4月12日整一天,“鹦鹉螺号”船只向荷兰海岸靠近,接近马罗尼河口。那里生活着好几群以家庭为小组的海牛,这些海牛像海马和大海马一样,属于人鱼目。这些美丽、安详、温顺的动物,长6至7米,体重至少有4000公斤。我告诉尼德·兰和康塞尔,有远见的造物主赋予这些哺乳动物一个重要的角色。的确,正是它们,像海豹一样,以海中的海草为食,把阻塞热带河流出海口的大面积海草消灭掉。
“你们知道吗,”我补充说,“当人类差不多将这些有用的动物种类统统消灭光时,会有什么后果吗?那就是,腐烂了的海草就会毒化空气,而有毒的空气,会导致黄热病,使这个富饶的地区变得一片荒凉。而有害的植物就会蔓延滋长在这片酷热的海里,疾病就会不可抵制地从普拉塔的里约河口一直蔓延到佛罗里达。”
但如果按杜斯耐尔的观点,这种灾难,比起海里的鲸鱼和海豹数量减少而带给我们的后代的灾难来说,那还不算什么。因为现在海里不再存在着那些“上帝派来清扫海面的大胃口动物”,海洋里到处充斥着章鱼、水母和枪乌贼,海洋将变成一个巨大的疾病传染源。
然而,尽管明了这些道理,“鹦鹉螺号”船上的人还是捕捉了6只海牛。这其实是为了充实船上的食品储备,这种美味的海牛肉比牛肉和小牛肉还好吃。但这样的打猎并没有什么意思,因为这些海牛面对捕捉丝毫不做反抗。就这样,几千公斤的肉被晾得干干的,放进船内库存起来。
这一带海域的物产丰富,那一天,另一次大规模的捕鱼又使“鹦鹉螺号”船上的食品储备大增。船上的鱼网捞上来了很多头上隆起一块椭圆形肉边骨片的鱼。那是属于亚鳃软骨目第三科的铆鱼。它们身上的扁平圆盘是由活动的横软骨组成的,这种鱼可以在这些软骨之间造成真空,使自己能像吸盘一样吸在物体上。
我在地中海观察过的印头鱼就属于这一类。但这里的这一类,是这一海区特有的软骨鮣鱼。我们的水手一捉到这些鱼,就把它们放进盛满海水的桶中。
捕鱼结束了后,“鹦鹉螺号”船只就向海岸靠近。在那个地方,有不少海龟睡在水波上。但要想捉到这些珍贵的爬行动物是很困难的,因为稍微有动静,它们就会醒过来,而且它们坚硬的甲壳不怕鱼叉攻击。但用鮣鱼就可以特别有保障并准确地捕捉到海龟。实际上,鮣鱼是一个活鱼钩,它会给淳朴的钓鱼人带来好运和财富。
“鹦鹉螺号”船上的人在鮣鱼的尾巴上结了一个足够大、能保证鮣鱼自如活动的环,环上系上长绳,绳的一端系在船上。
然后这些鮣鱼就被投进海里。立刻,它们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们游过去吸在海龟的胸甲上。鮣鱼是非常固执地,它们宁愿被撕烂,也不愿意松开吸盘。于是,船上的人就把它们连着被它们粘住的海龟一块拖回船上。
我们就这样抓到了好几只宽1米、重200公斤的卡古安海龟。这种海龟的龟甲上布满一层层很薄,透明,褐色,带有白色、黄色斑点的角质骨片,这使它们变得更为珍贵。另外,从美食的角度来看,这种海龟像普通的甲鱼一样味道极佳。
我们在亚马逊河口海域的停留以这次捕龟行动结束而告终,夜幕降临,“鹦鹉螺号”船只又回到深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