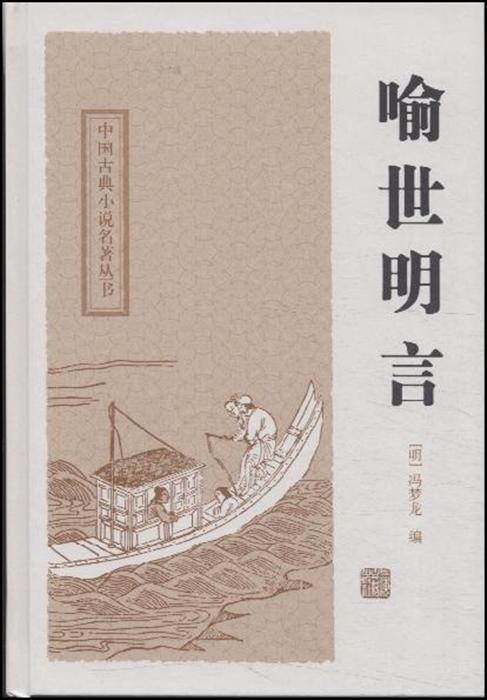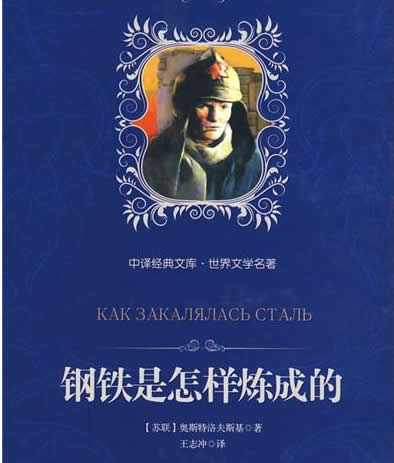- 第一章 印度洋
-
珊瑚墓地那感人的一幕深深地烙入了我的脑海,这次海底旅行的第一阶段就在那里结束。现在开始的是第二阶段的旅行。正是这样,尼摩船长的毕生都在这广袤的海洋中度过,他甚至已在那深不可测的海底中为自己准备好了墓穴。在那个地方,不会有任何海怪来骚扰“鹦鹉螺号”船上这些患难之交、生死与共的船员们的安眠。“也绝不会有人来骚扰我们的,”船长补充说。
对于人类社会,这位船长总是流露出他那种一直无法改变的不信任和愤懑的情绪。
至于我,我再也不满足于康塞尔他那些引以为豪的种种猜测。这位可贵的小伙子坚持认为,“鹦鹉螺号”船上的这位指挥官是被埋没的学者之一,他用蔑视的态度看待人世间的世态炎凉。他还是一位不为人所理解的奇才,由于对陆地上的一切非常失望,才不得以逃避到这个世人难以到达、而他的本性可以得以自由发挥的地方。但依我看来,这种猜测只能解释尼摩船长性格的一个方面。
确实,我们被关押在房中且被强迫睡眠的那个神秘的晚上,船长极其粗暴地从我手中夺走了我正准备向天际观望的望远镜的那种防范举动,“鹦鹉螺号”受到无法解释的撞击而导致了那个水手致命的受伤,这一切事实,都促使我向一种更合乎情理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尼摩船长不只是在逃避人类!他那神奇的装备不仅仅是为他追求自由的天性服务,而且还可能用于满足一种可怕的报复念头,这种念头我至今还不知道是何原故。
目前,一切还尚未清楚。我只是在一片黑暗中看到了几丝光亮。因此说,我仅仅是在叙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再说,我们没有受到尼摩船长的任何约束。因为他知道逃出“鹦鹉螺号”是不可能的。甚至因为我们没有承诺要履行什么诺言,口头上我们不是囚犯。可是,我们仅仅是礼貌上的客人,而实际上,是俘虏或者说是囚徒。因此,尼德·兰还没放弃恢复自由的希望。哪怕是偶然的机会,他也肯定会第一个抓住不放的。我当然也会像他那样的。可是,如果我把慷慨大方的船长让我们熟知的“鹦鹉螺号”船只的秘密带走,这对我不能不是一件憾事啊!总之,是该憎恨这个人呢,还是该赞美他?他是一个受害者呢,还是一个刽子手呢?再者,坦率地说,在永远离开他之前,我想完成这次海底旅行,它的开始是那么的奇妙。我想观察这一系列藏匿在这个星球海底里的奇观。我想看看这些人类还没看过的东西,即使要我以生命为代价来满足我那强烈的求知欲,我也会这样做的!可是,我们在太平洋底只走了6000里,至今为止我发现了什么?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
然而,我清楚地知道:“鹦鹉螺号”船只正在接近有人居住的陆地。一旦有逃脱的机会,我为了自己的好奇心而牺牲自己的伙伴,那未免太残忍了。我必须跟他们一起逃走,或者甚至指挥他们逃走。但这种机会会来临吗?被强行剥夺了自由的人急切地盼望着这个机会的到来,而作为学者或者好奇心强的人,我这时却徘徊不定。
1868年1月21日那天中午,大副从船里出来测量太阳的高度。我也登上平台,点燃了一支香烟,看着他操作。依我看,此人显然不懂得法语,因为我好几回大声地说出我的想法,如果他能听懂的话,他或许会下意识地作出某些反应,但他却仍然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当他用六分仪观测时,“鹦鹉螺号”上的一名水手——我们在克莱斯波岛进行第一次海底之游时,一直尾随着我们的那个身体强壮的人——也过来清洗探照灯玻璃。于是我仔细观察起这台灯的构造。灯里有一些凸状镜片,像灯塔的玻璃那样放置着,把灯光聚集在一个有效的面上,使亮度骤增百倍。电灯设计得如此的尽善尽美,使它的照亮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事实上,灯光是产生在真空中的,这就同时确保了它的稳定性和强度。而且,真空也可以减少石墨的消耗,灯的弧光正是从两根石墨棒之间产生的。节约对尼摩船长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不可能随意更新石墨棒。但在真空条件下,石墨棒的消耗速度是慢得几乎难以察觉。
当“鹦鹉螺号”船只准备继续它的海底旅行时,我回到了客厅。舱门重新关上了,“鹦鹉螺号”直接向西行驶。
我们在印度洋5.5亿公顷的广阔海域中劈波前进,海水如此的清澈透明,以致于人俯身看着水面时会感到一阵晕眩。“鹦鹉螺号”一般是在印度洋底100米到200米深处游弋。几天来一直都是这样。我对海有着一种深厚的情感。对于那些和我不一样的人来说,时间自然显得漫长而枯燥。而我则每天在平台上漫步,接受海洋新鲜空气的沐浴,透过客厅玻璃窗观看水中各式各样的景观,阅读图书室里的书籍,撰写我的论文。这一些就足以充实我的所有时间,我也就没有多余的一刻可以用来偷懒或自寻烦恼。
我们所有人的身体状况都非常好,也完全适应船上的特殊食谱。尼德·兰出于抵抗情绪,设法弄出各种菜式,我看这实在是没有必要的。此外,在这种恒温的状态下,我们甚至连感冒也不会染上。另外,石珊瑚草树,也就是法国普罗旺斯有名的“海茴香”,在船上还有一定的贮存,把它放在煮烂的珊瑚虫肉里,还是一剂治咳的良方。
好几天来,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水鸟、蹼足类动物、大海鸥和海鸥。有些水鸟被我们巧妙地杀死,再经过精心的烹制,就成了一道令人垂涎欲滴的水禽佳肴。那些从各个陆地上飞来的、作长途飞行的海上水鸟,因长途跋涉,停在水波上休憩。在它们里面,我就看见了属于长翼类、美丽非凡的信天翁,它们发出阵阵的鸣叫,就像驴叫那样不协调。蹼足家族的代表是善于在水面快速捕鱼、飞行速度极快的军舰鸟和数目繁多的鹲,或一种叫“稻草尾”的鹲,在鹲中,这类鹲身上长有红色条斑,身体和鸽子一般大小,白色的羽毛略带有一点玫瑰色,这就使它羽翼上的黑色尤为显目。
“鹦鹉螺号”船上的鱼网还捞起了好几种海龟。它们的背部隆起,龟甲十分珍贵。这类善于潜水的爬行动物翕上鼻腔外孔的肉阀,就能长时间地呆在水里。这些海龟中有几只被捉住时,还缩在龟壳里睡觉呢,它这一招还可以抵预海里动物的袭击。总的来说,这些海龟的肉吃起来马马虎虎,但它们的蛋却是一味可口的佳肴。
至于鱼类,当我们透过敞开的嵌板窥视它们神秘的海底生活时,不由得发出声声惊叹。我注意到了好几类我以前从没看过的鱼。
我特别要提到的是红海、印度海和赤道美洲一带海域里盛产的牡蛎。这类海底动物像海龟、犰狳、海胆、甲壳动物一样,身上披有一层既不是白垩质也不是石质,而是真正的骨质的护甲。它们的甲壳有立体三边形的,也有立体四边形的。在立体三边形甲壳的牡蛎中,我可以举出其中几个种类,它们身长半分米,肉富有营养,美味可口,尾部棕色,鳍部黄色。我甚至想把它们引进到不少海鱼都能很容易适应的淡水中养殖。我还看到了一些立体四边形的,背部长有4个粗节的牡蛎;一些身体下部长有花白斑点,可以像鸟类一样被驯养的牡蛎;一些身上的骨质甲壳突出成刺的三角牡蛎,它们因为叫声呼噜呼噜地,很奇特,而又被称为“海猪”;还有一些肉很丰厚、堆成锥形的单峰牡蛎,这种牡蛎的肉粗而硬,相当难啃。
在康塞尔的日记中,我还可以列举出他记录下的这一带海域中特有的单鼻鲀类动物,如红背鱼;身上有三道纵纹的白腹针鱼;长7英寸、色彩鲜艳的电鱼。其次是身上长有白色条纹、无尾,样子犹如一只黑褐色的蛋的卵鱼,这类鱼是其他鱼类的样本;还有称得上是真正的海底豪猪的鱼虎,它浑身长刺,身体一鼓,便形成了一个长满利刺的刺球,和各大洋都有的海马;唇长,鳍像双翅一样宽大,算不上是飞行但至少是会飞跃的海蛾鱼;尾部布满鳞片,体形扁平的鸽子鱼;身长25公分,色彩绚丽,味道鲜美的长颌鱼;头部凸凹不平的青灰色美首鱼;无数的身有黑纹,腹鳍长,能在水面以惊人的速度滑行的鳚鱼;味道鲜美,能扬起腹鳍顺流而下的风帆鱼;造物用黄、天蓝、银白和金黄各种色彩装扮起来的色彩斑斓的彩鱼;鱼翅成丝状的绒翼;身上沾着泥沙,能发出某种嗯嗯声的杜父鱼;肝脏有毒的鲂鮄;眼睛上罩着一个会动的眼泡的波帝恩鱼;最后是嘴尖长如管的哨子鱼,这位海洋中真正的猎手,有着一支夏斯波公司或雷明顿公司都设计不出的长枪,它每从嘴枪里射出一滴水,就能杀死一只虫子。
按拉塞拜德的划分法,第89种鱼属属于骨质鱼类第二次纲,其特征是有一块鳃盖和一片鳃膜。我就看到这一鱼属里的鲉鱼,它头上长有长刺,仅有一个脊鳍。按这种鱼所属的次属中说,它们有的身上长有鳞片,有的没有。第二次属同时向我们展示了一些身长3至4分米的二指鱼图样,这种鱼有黄色条纹,头部古怪。在第一次属里,则提供了一类名曰“海蟾蜍”的怪鱼的好几张样本。此鱼头大,时而布满深深的皱纹,时而隆起很多泡,长有细刺和结节,有一些不规则的可怕的角,浑身长满小茧,被它扎伤是很危险的,这是一种令人生厌而又令人生畏的鱼。
1月21日至23日,“鹦鹉螺号”船只每天走250里,即540海里,速度为每小时22海里。我们之所以能认识各种各样过路的鱼类,是因为鱼类受到电光的吸引,奋力追随我们。它们大部分跟不上“鹦鹉螺号”的速度,不久就落到后面了;而有些则可以紧跟着“鹦鹉螺号”好一段时间。
24日清晨,在南纬12.5度、东经94.33度上,我们望到了一个长满可可树的珊瑚岛——奇林岛。达尔文先生和菲特兹华船长就曾经来过这里考察。“鹦鹉螺号”船只贴着这个荒岛的悬崖峭壁行驶。船上的拖网网上来了许多珊瑚虫和棘皮动物,还有软体动物,各种各样怪异的贝壳。一些珍贵的珊瑚成了尼摩船长的宝贝,我看见了其中有一种星点状的、寄生在贝壳上的珊瑚骨。
过了一会儿,奇林岛在天际边消失了,“鹦鹉螺号”船只向西北方向的印度半岛尖端驶去。
“这是一片开化的陆地,”那天尼德·兰对我说,“与野人多过狍子的巴布阿岛相比,这里好多了!教授先生,印度这片陆地上,有公路、铁路,还有英国、法国和印度的城市。5里路内,我们总不会碰不到一个同胞吧。嗯!难道这不是与尼摩船长撕破脸皮告辞的时机吗?”
“不,尼德,不,”我口气坚决地说,“就像你们水手说的吧:让我们继续上路吧。‘鹦鹉螺号’船只会接近有人居住的陆地,它就总有一天会回到欧洲的。就让它带我们回去吧。一旦到了我们的欧洲海域,我们再见机行事。再说,我估计尼摩船长不会像在新几内亚森林里那样,允许我们到马拉马尔或哥罗蒙代尔海边打猎的。”
“那这样,先生,不经他允许不行吗?”
我没有回答加拿大人。我不想争辩下去。其实,是命运让我到了“鹦鹉螺号”船上,我心底里会一直考虑着命运中这些偶遇的。
从奇林岛起,船的速度总的来说是放慢了。航行的线路也比较随意,船经常下到很深的海底。船员好几次用船内的纵斜机板把船的斜面板转动到吃水线处。我们就这样一直沉到2至3公里深的海底。对于这片广阔的印度洋深海,潜水深度13000米的探测器尚不能到达,我们也没加以勘探。至于深海层的温度,船上的温度计总是显示在零下4度。我只是注意到,在海水表层,低层的水总比海面的水冷。
1月25日,洋面一片荒凉,“鹦鹉螺号”船只在海面上行驶了一整天,轮机有力地拍打着水波,喷出束束水花。瞧,这样人们怎不会把它当做一只巨大无比的鲸鱼呢?这一天四分之三的时间里,我逗留在平台上,望着大海,天际边空无一物。只是到了下午4点左右,一艘长长的蒸汽轮朝西迎面开来。有一阵子,我清楚地看到了蒸汽轮的桅杆,而蒸汽轮却察觉不到贴着水面行驶的“鹦鹉螺号”船只。我想这是印度半岛和东方汽轮公司的蒸汽轮,它航行于锡兰与悉尼之间,途中曾在乔治王角和墨尔本港停靠过。
下午5时,热带地区短暂的黄昏来临之前,海上出现了一种奇妙的景观,康塞尔和我都对此赞叹不已。
那是一种可爱的动物。按古人的说法,遇上它就意味着好运。亚里士多德、阿德尼、普林、奥彼恩曾经研究过这种动物的嗜好,并用意大利学者和希腊学者诗篇中所有富有诗意的言辞来形容它,称它为“鹦鹉螺”和“旁比里斯”。但现在的科普书上不采用这种叫法,而是称这种软体动物为船蛸。
问过康塞尔的人都会从这位正直的小伙子那里得知软体动物支分为五纲。第一纲头足纲动物,它们有的有介壳,有的没介壳;头足纲动物按鳃的数目分为两鳃和四鳃两个科;两鳃科又分船蛸、枪乌贼、墨鱼三属,四鳃科则只有鹦鹉螺一属。按这种分类术语,如果还有顽固不化的人把带吸盘的船蛸和带触须的鹦鹉螺混为一谈的话,那可就不能原谅了。
这么说,当时有一群船蛸正在海面上漂游着,估计有成百上千只。这些船蛸属于长有结块的那类,是印度洋特有的。
这些动作优美的软体动物吸进一管水,再把水射出来,借助水的反作用力向后游动。它们有8条触须,细长的6条漂浮在水面,而另外2条则竖起弯成掌状,像风帆一样迎风舒展。我清晰地看到了它们螺旋状的波纹介壳,居维埃确如其当地称它们为“精巧的小舟”。这真是一叶真正的小舟啊!船蛸用分泌液做出自己的外壳,它不把外壳粘在身上,可外壳却时刻装载着船蛸。
“船蛸本来可以自由地离开介壳,”我对康塞尔说,“但它却从没离开过。”
“尼摩船长就是这样的,”康塞尔说得对极了,“所以他觉得最好把自己的船叫做‘鹦鹉螺号’。”
“鹦鹉螺号”船只在这群软体动物之间漂浮了大约一个钟。突然,这群软体动物不知道受到了什么惊吓,它们好像听到了一声信号似的,所有的风帆骤然放了下来,爪子收回去,身体卷缩,介壳翻了个身,调转重心,整个小船队消失在茫茫的海波中。这一切就发生在一眨眼间,我还从没见过一支船队能像它们一样,这么协调一致地行动。
这时,夜幕骤然降临。微风费力地掀起的阵阵水波,在“鹦鹉螺号”的船舷顶列板下静静地延伸着。
第二天,1月26日,在子午线82度处,我们穿过了赤道,又回到了北半球。
在这整整一天里,一群令人生畏的角鲨紧紧尾随着我们。这是一种可怖的动物,它们在这一带海域里迅速地繁殖,使这里的海区变得十分危险。烟色角鲨背部褐色,腹部灰白,武装着11排尖牙;“眼睛”角鲨在颈部处有一大块被白色圈起来的黑斑,看上去就像是一只眼睛;灰黄色角鲨的喙部显圆形,身上布满暗斑。这些力大无比的动物不时用力地撞击着客厅的玻璃,让人担心不已。尼德·兰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他真想冲到水面去,用鱼叉射击这些庞然大物。特别是某些嘴巴里像嵌地板砖一样布满了牙齿的星鲨和一些长达5米的大虎鲨,更使他怒不可遏。但过了一会儿,“鹦鹉螺号”船只加快马力,轻松地把这些速度最快的鲨鱼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1月27日,在孟加拉湾的出口处,我们好几次见到了一幕幕阴森可怖的景象!一具具尸体漂浮在水面上。这是印度城市中的死尸,被恒河水冲入大海中。秃鹫——这个国家唯一的收尸人,还没能把这些尸体狼吞虎咽完。而在这里,并不缺少角鲨来帮它们完成这项收尸工作。
晚上7点钟左右,“鹦鹉螺号”半浸在乳白色的海水中行驶着。一眼望去,海水好像牛奶似的。这难道是月光的杰作吗?不,在太阳的余辉中,才两天的新月还在海平面以下呢。整个天空中,虽然星光灿烂,但和银白色的海水相比,似乎显得有些黯淡。
康塞尔一点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问我这种奇特的现象是什么原因。幸好,我还能回答他的问题。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乳白色的大海’,”我对他说,“在盎波尼岛海岸和这一带沿海经常可以看到广阔的白色波浪。”
“可是,”康塞尔说,“先生可以告诉我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吗?我想该不是这里的海水都是牛奶做的吧!”
“不,小伙子,这让你惊讶的白色是因为水中有成千上万条细小发光的纤毛虫。这些虫胶质无色,像一根头发那么细,长不到五分之一毫米。这些纤毛虫相互粘在一起,延伸在好几海里的海面上。”
“好几海里哪!”康塞尔叫了起来。
“是的,小伙子,不要费尽心思去算这些小虫了!况且你算不出来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些航海家曾经漂流过40多海里‘乳白色的海’。”
我不知道康塞尔是否会采纳我的建议,但他好像陷入了沉思之中,他可能正在努力地计算着40多海里究竟能有多少五分之一毫米的小虫。至于我呢,我继续观察着这一现象。在几小时内,“鹦鹉螺号”的船头划破着这股白色的海流。我注视着它静静地在皂沫般的水面上滑行,就像漂浮在海湾的顺流和逆流相遇交叉时引起的白色泡沫旋涡中一样。
临近午夜,大海突然恢复了它平常的面貌。但在我们后面到海平线尽头处,天空映射着白色的水波,似乎久久沐浴在模糊的北极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