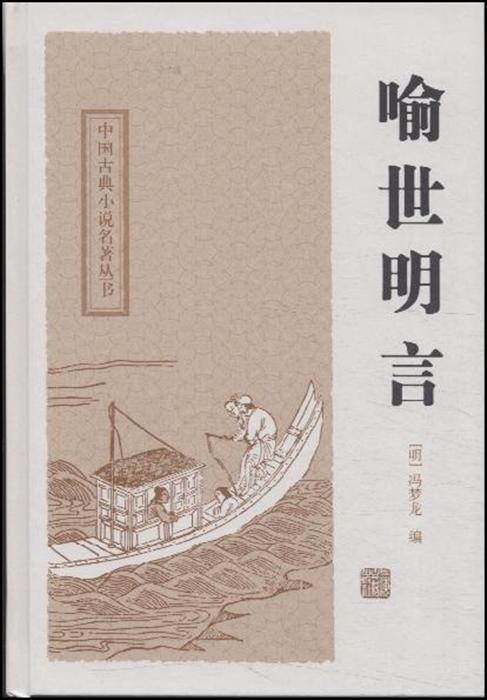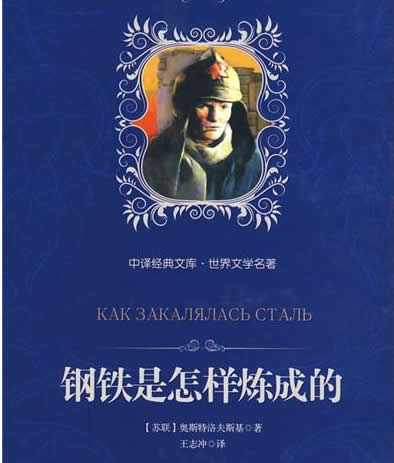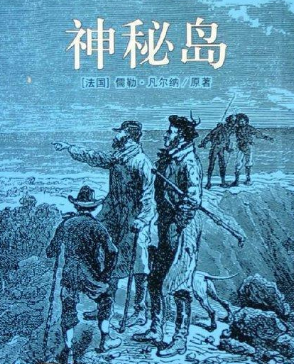- 张佐
-
张佐
开元中,前进士张佐常为叔父言,少年南次鄠杜,郊行,见有老父,乘青驴。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颜甚悦怿,旨趣非凡。始自斜迳合路。佐甚异之。试问所从来,叟但笑而不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岂盗贼椎埋者耶,何必知从来?”佐逊谢曰:“向慕先生高躅,愿从事左右耳,何赐深责?”叟曰:“吾无术教子,但寿永者,子当嗤吾潦倒耳。”遂复乘促走,佐亦扑马趁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寝未熟,佐乃疲,贳白酒将饮,试就请曰:“单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之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饮讫,佐见翁色悦,徐请曰:“小生寡昧。愿先生赐言,以广闻见,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之所见,梁隋陈唐耳,贤愚治乱,国史已具,然请以身所异者语子。吾宇文周时居歧,扶风人也,姓申名宗,慕齐神武,因改宗为观。十八,从燕公子谨征梁元帝于荆州,州陷,大将军旋,梦青衣二人谓余曰:“吕走天年,人向主,寿不千。”吾乃诣占梦者于江陵市,占梦者谓余曰:“吕走回字也,人向主住字也,岂子住乃寿也。”时留兵屯江陵。吾遂陈情于校尉拓跋烈,许之,因却诣占梦者曰:“住即可矣。寿有术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术蕊散。多寻异书。日诵黄老一百纸,徙居鹤鸣山下,草堂三间,户外骈植花竹。泉石萦绕。八月十五日,长啸独饮,因酣畅。大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岂无异人降止(止原作旨,据明抄本改)。”忽觉两耳中有车马声。因颓然思寝。头才至席。遂有小车,朱轮青盖,驾赤犊,出耳中,各高三二寸,亦不觉出耳之难,车有二童,绿帻青帔,亦长二三寸。凭轼呼御者,踏轮扶下,而谓君胄曰:“吾自兜玄国来,向闻长啸月下,韵甚清激,私心奉慕,愿接清论。”君胄大骇曰:“君适出吾耳,何谓兜玄国来?”二童子曰:“兜玄国在吾耳中,君耳安能处我?”君胄曰:“君长二三寸,岂复耳有国土,傥若有之,国人当尽焦螟耳?”二童曰:“。胡为其然,吾国与汝国无异。不信,请(请原作尽,据明抄本改)从吾游,或能便留,则君离生死苦矣。”一童因倾耳示君胄,君胄觇之,乃别有天地,花卉繁茂,甍栋连接。清泉萦绕,岩岫杳冥。因扪耳投之。已至一都会,城池楼堞,穷极壮丽。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顾见向之二童,已在其侧,谓君胄曰:“此国大小于君国,既至此,盍从吾谒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墙垣阶陛,尽饰以金碧,垂翠帘帷幔。中间独坐。真伯身衣云霞日月之衣,冠通冠,垂旒,皆与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执白拂,一执犀如意。二人既入,拱手不敢仰视,有高冠长裾缘绿衣人,宣青纸制曰:“肇分太素,国既有亿。尔沦下土,贱卑万品,聿臻于如此,实由冥合,况尔清乃躬诚,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为主箓大夫。”君胄拜舞出门,即有黄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识,每月亦无请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当便供给。因暇登楼远望,忽有归思,赋诗曰:“风软景和煦,异香馥林塘。登高一长望,信美非吾乡。”因以诗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质性冲寂,引至吾国,鄙俗余态,果乃未去。乡有何忆耶?”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视,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旧去处。随视童子,亦不复见。因问诸邻人,云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数月,未几而君胄卒。生于君家,即今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以得到兜玄国,然俗态未尽,不可长生,然汝自此寿千年矣。吾受汝符,即归。”因吐朱绢尺余,令吞之,占者遂复童子形而灭。自是不复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兹向二百余岁。然吾(吾原作无,据明抄本改。)所见异事甚多,并记在鹿革中。”因启囊,出二轴书甚大,字颇细,佐不能读,请叟自宣,略述十余事,其半昭然可记。其夕将佐略寝,及觉已失叟。后数日。有人于灰谷湫见之,叟曰:“为我致意于张君。”佐遽寻之,已不复见。(《出玄怪录》)
【译文】
开元中年,前科进士张佐,常跟叔父讲述那个自己亲见亲闻的故事。
张佐少年时旅居南方鄠杜,一次在郊外走路,看到一个老头儿,骑着四蹄雪白的青驴,背着鹿皮包,和颜悦色,旨趣非凡。刚从小路走上大道,张佐对他颇为惊异,试探着问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老头儿听了只是笑而不答。张佐再三询问,老头儿突然愤怒地呵叱道:“好你个少年小子,竟敢如此相逼!我难道是死了椎埋起来的盗贼不成,有什么必要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张佐谦逊地致礼说:“只因一向仰慕先生的行迹高超,甘愿在您身边服务而已,为什么如此严厉地责备我呢?”老头儿说:“老朽并无什么法术可以教给你,我只是个长寿的人,你恐怕是在嘲笑我年迈潦倒罢。”说完又骑上驴急急奔去,张佐也跳上马去追赶他,两人都到客店里住下来,老头儿枕着鹿皮包还没睡熟,张佐因疲劳赊了白酒要喝,便试探着邀请老头儿说:“就用这一只瓢请先生与我共饮。”老头儿跳起来说:“这正是我的爱好。你怎么如此了解我的心意呢!”酒喝完后,张佐见老翁满脸喜悦,便小声请求道:“小生愚昧寡闻,愿听先生赐言以广见闻,不敢有什么别的非份之想。”老头儿说:“我所见到的,不外是梁隋陈唐几代的事情罢了,其中的贤愚和治乱,在国史书上都已记载;我只把与史书不同的亲身经历讲给你听听吧。我在宇文周时居住于岐地,是扶风人,姓申名宗,因仰慕齐代神武而改宗为观。十八岁时跟从燕公子谨到荆州去征伐梁元帝,荆州攻陷后大将军凯旋而回,我与部队留守在江陵。有一天,梦见穿着青衣的两个人对我说:‘吕走天年,人向主,寿不千。’我便到江陵市去找占梦的,占梦的对我说:‘“吕走”,“回”字也;“人向主”,“往”字也。岂不是说你回家居住便能长寿吗?’当时留下的兵驻扎在江陵,我便向校尉拓跋烈陈情返乡,被批准了。我又到占梦的那里去告别说:‘回家去住已经可以了,要想长寿还有什么方法呢?’占梦的说:‘你的前身是梓潼的薛君胄,好服用道术炼制的药散,多寻奇异之书,日诵黄老一百页,迁居于鹤鸣山下,有草堂三间,门外遍植奇花修竹,有泉水与山石。萦绕在其中,有一年的八月十五日,一个人坐在那里长啸独饮,喝到酣畅时高声喊道:“薛君胄疏淡若此,难道没有异人降临到我的面前!”忽然觉得两只耳朵里有车马的声音,于是颓然想睡。脑袋刚刚沾席,便见眼前出现了小车,红色车轮青色车盖,前面驾着红色的牛犊,小车从自己的耳朵里出来,各高两三寸,也不觉得从耳朵里出来时怎么困难,车上有两个小童,绿头巾青披肩,也是长两三寸,依着车上的栏杆呼唤车夫,踏着车轮扶下车后对君胄说:“我们从兜玄国来,以前听到您长啸于月下,声韵十分清彻激越,内心深表敬慕,很愿接受您的清高之论。”君胄大惊道:“你们刚才从我的耳朵里出来。怎么说是从兜玄国来呢。”二童子说:“兜玄国是在我们的耳朵里面,您的耳朵里哪能住下我们?”君胄说:“你们的身长只有二三寸,哪能再在耳朵里有国土。就算有的话,那么国人也该都是干巴小虫罢了。二童说:“怎么能那个样?我们国家与你的国家并无不同。如果不信就请跟着我们去看看,有可能就留在那里,那您脱离了生死之苦了。”一个小童便侧过耳朵来让君胄观看,君胄往里面一瞧,但见别有天地,花卉繁密茂盛,瓦屋一栋接着一栋,清泉盘旋萦绕,山崖高耸入云。于是摁下自己的两耳走了进去,很快便来到一个都会,只见城池楼阁,无比壮观华丽。君胄正彷徨于街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在向周围张望时看见原先见过的那两个小童已经站在自己身边,小童对君胄说:“这个国家与你的国家相比,到底哪个大哪个小?既然到了这里,何不跟我们去拜见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住在一座大宫殿里,墙壁与台阶都装饰得金碧辉煌,室内挂着翠帘帷帐。蒙玄真伯端坐在正殿中央,身穿绣满云霞日月的锦绣衣服,头上戴着通天冠,冠上下垂的流苏可与身体等长。四个玉童侍立在真伯左右,一对手执白拂尘,一对手执犀角如意。小童与君胄走进大殿之后,个个拱手行礼不敢抬头仰视,一个头顶高帽身穿长裙围着绿衣服的人走上前来,高声宣读青纸文书道:“肇分太素,国既有亿。尔沦于下土,贱卑万品,聿臻于如此,实由冥合,况尔清乃躬诚,叶于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为主箓大夫。”君胄起舞拜谢,然后走出门来,门外有身着黄帔的三四人给他引路,领到一处官署。这里面的文牍簿册他大都不能认识,每月也没有人前来请示和领受什么,但只要他心里想的东西,没等自己开口吩咐,身边的侍从便预先知道,当即奉献上来满足他的需求。一日闲暇无事,他便登楼远望,忽然产生了回归故乡的念头,提笔赋诗道:“风软景和煦,异香馥林塘。登高一长望,信美非吾乡。”写成后送给两个童子传阅,不料童子愤怒地说:“原以为你性情冲淡平静,所以引渡到我们国家,没想到你的鄙俗余态,至今仍未除去。故乡有什么值得怀念的呢?“说完急忙驰逐君胄。君胄觉得好似从什么地方落到了地上,抬头一看,原来是从童子的耳朵里掉落下来,依然回到了旧地方。回头再看童子时,已经踪影全无。询问各位邻居,都说君胄已失踪七八年了,而君胄在那边仅仅住了几个月,没过多久君胄便去世了。后来又出生在君家,也就是现在的他。”占梦的又说:‘我的前身就是从耳朵里出来的那个童子,因为你的前身爱好道术,所以能到兜玄国去,但因你俗态尚未脱尽,不可长生不老;然而自此以后你可长寿一千年。我交给你符箓之后,立即回去。’说完。从嘴里吐出一尺多长的红绢子,令我吞下,占梦的随即恢复童子原形而幻灭了。从此之后我再不生病,周游了天下的名山,至今已经活了二百余岁,见到的奇异事情非常多,都记载在鹿皮包里呢。”说着,老头儿就去打开鹿皮包,取出特别大的两轴书,字极细小,张佐不能认读,便请老头儿自己宣讲,老头儿约略讲述了十余件事,其中一半明了可记。那天夜晚张佐听完老头儿讲的故事之后,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醒来一看,老头儿已失踪了。过了几天,有人在灰谷湫看见过他,他说:“替我向张佐致意。”张佐听说后,急忙去找他,但已在也看不到他了。